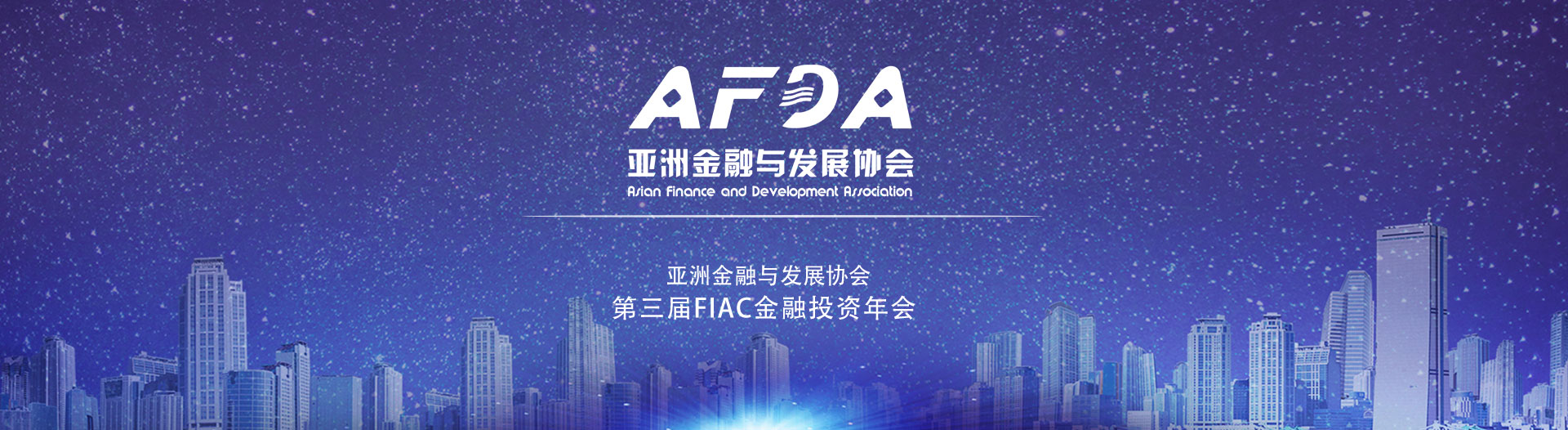
文章来源:亚洲金融与发展协会 发布时间:2023-01-19 17:16:04
2022年,全球疫情跌宕反复,地缘冲突持续不断,旧世界秩序正分崩离析,新全球秩序前路迷茫。面对这些新形势、新变化,中国需面对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中国新形势:挑战与应对”相关专家学者就该话题展开探讨。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尽管受全球疫情影响,但实际上我国的出口远远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前三季度GDP增长放缓到3左右,但其中有1.1个百分点来自于出口。言外之意,到目前为止,在疫情期间实际上出口是支撑整体经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柱。但面临目前全球通胀的风险,可能明年整体全球的需求会出现明显放缓,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出口将会遇到下行的压力。因此我们的确要尽快的、更高效去协调防疫和经济恢复,需要内需补缺口,消费也好、投资也好,要加力去做。
屈宏斌指出,在未来几年看远一点出口还面临另一个层面的挑战,那就是疫情以后所引发的产业链安全、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个将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带来直接冲击。这方面的挑战可能比短期需求的收缩更严峻,因为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挑战,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实际上要稳住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往大了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未来要保住产业链的地位、市场份额,就要在制造业方面继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继续吸纳更多的就业,这是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一个很大的门槛,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多地脱虚向实,重归制造业。
那又该如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关于怎样提升消费,我想提一点,要更多关注对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部分。消费增长越来越多的和消费结构升级有关。现在的消费和过去的消费有很大区别,过去我们主要是衣食住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但是现在转变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新的包括金融这些领域后,它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和公共服务直接相关,但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没有跟上步伐,实际上限制了这部分的消费。
刘世锦指出,扩大需求还呈现在投资的增长。制造业投资相对比较稳定,但目前增长比较快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这个领域的制造投资。电气机械制造、仪器仪表,还有汽车制造等等,总的来讲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些领域的制造业的投资,现在整体增长比较快。另外,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其实去掉基建以后,服务业投资是最近几年增长相当快,而且很稳定,包括在最近两年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服务业投资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韧性很强,而且略有增长。而服务业投资包含的也是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金融、商务服务等这些领域。
刘世锦说:“其实我刚才讲的消费的增长它主要是医疗、教育、社保等等这些,它实际上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密切相关,刚才讲了需要和基本公共服务相配合。我们可以讲它是消费,没问题,同时它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我想强调一个观点,消费也是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是比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投资。”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产业研究院院长沈明高表示,到目前为止,全球主要的机构对未来长期的全球增长的预测,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基本上都隐含一个重要的我认为是关键的假设,未来全球区域增长的动能主要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在中国很难靠出口维持比较快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应怎样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刚刚谈到的消费,我非常赞同。到2050年,中国的消费实力会接近美国的50%左右,这里面取决于我们对美国增长的假设,意味着我们居民消费未来实际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年均增长出口大概在6%-8%,我认为这个假设方向非常正确,中国未来要靠消费。
沈明高总结道:“我们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提质增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点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即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第二点,要实现一个量的合理增长,我们大概要实现4.7%每年的增长,所以在短期来讲,稳增长有其紧迫性;第三点,提质是实现增长可持续的前提,提质的直接标志是相对强势的本币,相对强势的本币实际上有利于推动人民币资产的重新估值,使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的核心资产。”
眼下,国际形势风高浪急,中美关系更成为重中之重。IFF学术委员、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表示,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形势其实非常严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一些是有利的因素,比如说二战以来的既有的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可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正在被重塑,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东升西降,国际治理体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些都是正面的变化。但我们可能忽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时期,它的挑战是非常大。对中国发展的挑战,最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我们和西方的关系,我们过去比较舒服的这种以出口为主导或者是参照国际大循环的方式,可能难以为继,要做一些新的思考。
胡伟星指出,应对国际局势对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关键是要抓住龙头,就是中国要抓住中美关系这个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是影响我们外部环境的一个重大的因素。目前由于世界经济的环境恶化、高通胀,俄乌战争带来了金融市场、能源市场的的动荡,美国的市场越来越差,所以拜登政府开始考虑稍稍缓和一下和中国的关系。巴厘岛的中美首脑会议,有了元首外交在一些大的底线上的共识,双方知道各自的意图,可以向下传导,在技术层面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对话。比如说在经贸方面,美国财政部的经贸团队也跟中方进行接触,还有商务部、贸易,还有军方等等,都开始和中国进行工作层面的接触,我觉得这是好的势头,我们希望这种势头能够维持下去,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和美国民间的中美文化的交流,这样双方不至于脱钩,脱钩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局下,中国必须要克服种种挑战,变压力为动力,把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做得更高水平,那么这个机遇就在眼前。